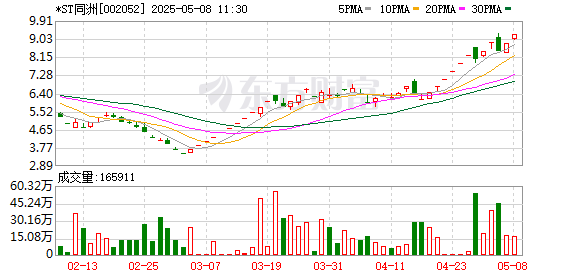来源:滚动播报配资网前十名
(来源:上观新闻)
史禄国是享誉世界的俄国人类学家,国际公认的通古斯研究权威。他在中国度过了自己学术生命最成熟、最旺盛的17年,一生中绝大部分著作在中国出版,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界的影响深远,贡献卓著。
近期出版的新书《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在广泛搜集、整理史氏在华活动资料的基础之上,详细梳理、研究史氏在华期间的学术研究,以及他与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苏柯仁等中外知名学人的交游活动,深入探讨史氏与中国学界的交往,客观评介其人类学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研究的学术贡献,进而观察并剖析人类学在初入中国时所面临的各方不同态度及其发展境遇,为国际学界的史禄国学研究提供了一张来自中国的学术拼图。
展开剩余85%经师与人师:与费孝通的师生情谊
众所周知,费孝通是史禄国在华唯一及门的弟子,中国学界早期对史禄国的了解主要归功于费氏不遗余力的引介。1939年,费氏《江村经济》在伦敦George Routledge & Sons书局出版时,该书扉页对作者的介绍为“燕京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博士”。与之相对应的是,费氏在文前“致谢”部分特别感谢曾经鼓励和帮助他进行调查与撰写此书的人依次为吴文藻、史禄国和马林诺斯基三人,专门提到史禄国教授是其早年攻读人类学的老师。其实,在《江村经济》于英国出版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费孝通对史氏的生平与学术的了解并不多,直到 1991 年其在辽宁丹东鸭绿江边度暑期间访问了附近的满族村庄,方才勾起他在六十余年前曾读过老师《满族的社会组织》的记忆,继而萌生了对史氏满族调查进行追踪研究的想法。费氏假期结束回到北京后,随他同行的潘乃谷说服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高丙中参与满族的追踪研究。作为该课题的初步研究工作之一,高氏从图书馆借得《满族的社会组织》英文书,着手翻译工作。1993年底,该书稿译竟,预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是邀请费孝通为译著作序。然而,为自己的老师作序,费氏自认难逃师承越位之嫌,故他将在1994年2月完成的《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附于译著之后,深情回忆他在六十余年前于老师门下读书的点滴。可能是意犹未尽,同年4月,费氏继续阅读老师的体质人类学论著,又撰成《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体质人类学》,述其追随史氏学习体质人类学时的心得体会。
史禄国晚年在北平(20世纪30年代)
费孝通
这两篇忆文内容互相补充,对学界影响颇大,成为当下国内外学界研究史氏时的必引之作,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一是费孝通以第一视角回忆与史氏交往点滴,重新梳理了史氏在华活动的部分轨迹,让其在中国的学术与人生事略重现学界,人们惊叹这位几为中国学界淡忘的学者,竟倾力栽培了已闻名世界学坛的费孝通!二是费孝通以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勾绘出史氏在北平时的肖像:生活中,史氏不善交流,与世无争,是个“孤僻的隐士”,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性格上,他“生性怪癖”,是人们眼中难以相处、“高深莫测”的怪人;很少有人能读懂这位“世界级的学者”,加之他的英文表述差,传播面有限,与同时代的人类学家相比较,知名度最低。三是费氏以学生与读者的眼光与立场,与彼时西方学界的马林诺斯基、布朗、克虏伯等人类学家作横向的比较,深刻地讨论史氏体质人类学的思想与学术贡献。总而言之,史禄国在中西学界的个人形象,长期以来因费孝通两篇回忆文章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人不知而不愠”,不善沟通与表达,在彼时中西学界影响非常有限的深刻印象,费氏的论述成为学界研究史氏学术思想与成就的起点。
梳理史禄国与费孝通的师生情缘,要从两人认识的经过说起。1930年,费孝通放弃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此前一年,吴文藻甫自美国留学归国任教于该系,提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社会学要中国化”的学科发展新思路,欲培养一批学生从事中国本土社会学研究。为此目的,吴氏力邀年近七旬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派克于1932年9月至12月底在燕京大学开设“集合行为”“社会学研究班”两门课程,传授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彼时在燕大社会学系学习、即将毕业的费孝通成为拥护派克“社区研究”的积极分子,也是吴文藻欲重点培养的学生之一。
费氏翻译了派克的《论中国》,又发表《派克及季亭史二家社会学说几个根本的分歧点》,详细介绍派克生平学术、中国文化论,以及其与美国社会学家季亭史(F.H. Giddings,1855— 1931)两人所属学术派别及各自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对象共五点学术分歧。派克在中国逗留3个月后,便离开中国继续云游世界,吴文藻为继续他的“社区研究”计划,开始陆续策划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送往欧美各人类学重镇学习“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意将费氏送往英国追随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学习。在吴氏看来,要培养一个能进行社区调查与研究的社会学学者,首先应学会人类学方法,于是便想到与燕京大学毗邻的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唯一的人类学教授史禄国。当然,吴文藻安排费孝通拜师史禄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彼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不具备被推荐到国外留学的条件,而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便可获得赴欧美公费留学的名额。
成立于1926年的清华学校社会学系,由陈达担纲首任系主任。1928年秋,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校方确定社会学与人类学并重的学科发展原则,遂将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人类学系”,但彼时该系师资与课程并不完备。至1930年秋,始有增聘教授的举措,史禄国恰在此时入职该系,与傅尚霖、陈达组成该系的三驾马车,又增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兼职,讲授“社会思想史”课程。 1931年至1935年,又陆续聘请吴景超(1901—1968)、潘光旦(1899—1967)、李景汉(1894—1986)等人加盟该系,于是清华社会人类学系初具规模与影响,成功立足于国内学界。
1933年的暑假前夕,吴文藻偕同费孝通登门拜访史禄国,此行旨在说服“生性怪癖”、让人“敬而远之”的史氏当年招收人类学专业研究生。据清华大学1931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全校研究生招生名单显示(1934年暂停招收研究生),6年间,社会人类学系仅见1933 年招收费孝通一人为研究生。由此看来,正是这次会面(准确地说是口试)让费孝通得到了史禄国的肯定,进而努力从校方获取研究生招生名额,为费氏顺利进入清华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就在费孝通与史禄国正式见面前后,费氏已经通过阅读史氏的论著对其学术有所了解。1933年6月10日,费孝通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便引用了史禄国对中国人种有Α、Β、Δ 三个类型的结论,他在文中称史禄国的《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对中国迎亲问题的研究,令其印象特别深刻。翌年6 月,费氏在《社会学界》发表其本科学位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杂志编辑在正文前加的按语中说到,费氏用了三年的功夫,经吴文藻、顾颉刚、潘光旦、派克、史禄国等诸先生的指导与批评,五易其稿而成。
史、费两人见面后,史氏便为费氏量身定制了系统的人类学培养计划,其后无论是课程安排,抑或在学术实践方面,处处体现出他对费孝通人类学教育的“主意”与“心计”。史氏对费孝通的学术训练,始终贯彻着他的人类学学术思想。在费孝通看来,史氏将人类学的活体测量作为人类学学科的基础,通过体质测量深入对人体生理现象的观察,其体质人类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将人置于自然现象之中,把生物现象连接到社会文化现象上,再从宗教信仰进入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史禄国与马林诺斯基都是早期人类学功能派的代表,
二人不同之处在于:史氏的人类学出发点深植于人体的本身,将人体形态、结构与生理机制看作生物演化的一个阶段,从人类生理基础去阐明人类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而马氏则将生物基础的“食色性”行为看作满足人类生物需要的手段,并从此出发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功能与结构。不过,马氏仅止步于此,并未像史氏那样走进人的生理基础。两者相较,史氏的人类学视野与理论更为广博、深奥,思维的透视力更深远。
史氏为贯彻他的人类学教学理念,特将对费氏的培养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用时两学年:第一个阶段学习体质人类学,第二个阶段是语言学,第三个阶段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中间还需要学习考古学知识。很明显,史氏按照欧洲大陆与英美的人类学界的统一做法,认为人类学应包括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四大分支,这种分类既是英美人类学界通行的分类,也是民国以来中国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
原标题:《回溯费孝通的学术拼图,身后竟有一位俄国人类学家》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郑周明
来源:作者:王传配资网前十名
发布于:北京市冠达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